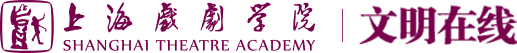近日,在我国大陆地区掀起了一股“梅兰芳”热潮:先是电影大片《梅兰芳》隆重登台;后是话剧《梅兰芳》在沪热闹开演;再是导演陈凯歌书籍《眉飞色舞》闪亮发行;接着是梅兰芳之子、梅派京剧传人梅葆玖日前现身上海万达影城,为推广首批限量电影专供版京剧唱片《太真外传》、《贵妃醉酒》举行观众见面会;还有就是研究梅兰芳问题专家翁思再的长篇文章“非常梅兰芳”(现已被作为专著出版)在众多报刊及时发表转载……一时间演梅兰芳、看梅兰芳、说梅兰芳、议梅兰芳变为了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
从传播学角度看,“梅兰芳现象”确实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思考之一: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戏曲艺术)的精髓在当代新形势下如何寻找适合受众审美心里的载体继承、弘扬?
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面临继承、弘扬的严峻课题,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除了出版有关的书籍和推行京剧进课堂等相关的方法之外,中央电视台也在用《百家论坛》这样的方式进行相关文化的传播。但是,从整体上看,我们的传统文化还面临着广大受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受众如何认识、熟悉、了解和喜欢的问题,特别在西方文化长驱直入的背景下,在“麦当劳”、“肯德鸡”、“圣诞节”、“情人节”“哈里波特”、“指环王”等西方文化强大包围下的国民生存环境中,不断教育我们的国民,使他们具备应有的民族气节、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就显得尤为重要,就这个意义上看,国家今年推出了清明、端午、中秋三个民族节日的法定休息日还是很有针对性的。
前两年,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焦晃在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中扮演了雍正老爸康熙一角而摘取“飞天”、“金鹰”两项桂冠,顿时,亿万观众惊讶:“我们大陆演艺界还有这么棒的好演员!”大家喜欢上这个常在话剧舞台上露面的焦老爷子。这让焦晃在高兴的同时也显得有些无奈:“我在舞台上扮演过许多角色,不见得就低于现在扮演的康熙。不过因为舞台的局限,不像电视剧有这样广泛的覆盖面。”
由此可见,一个作品、一个人物、以至一种观念等属于文化传播方面的事件,在当今世界要得到最大限度的推广和普及甚至弘扬,一定要运用现代人喜闻乐见的形式载体,一定要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一定要运用信息化社会对人审美心理的暗示和争引,正是在这个层面看,余秋雨多次强调的“我们现在做学问的人千万不能只躲在书斋里”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正是在这个层面看,张颐武的“在今天世界上章子怡比孔子的影响要大”的立论是有一定的、传播学的道理的。
用这个观点来看,我们至少在涉及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和民族艺术等主导观念的宣传、普及和弘扬方面,缺少是正是这方面有力的载体和手段。要么严肃有余、要么庸俗过头,我们始终难以在两者的结合和平衡上找到最佳的度。8个样板戏的推广,人家是下了大力气的,当然全国人民只有这些戏是荒唐的;但是,对它的反动,我们现在却连基本的、必须的、民族的包括戏曲在内的诸多艺术形态都不敢大张旗鼓地宣传和推广,那也是可悲的!
思考之二:在寻找到艺术家认为是合适的载体之后,是利用这个载体一味地迎合还是有意识地引领受众?
在艺术审美流派中,有一派叫“接受美学”,主要观点是:任何一件艺术品的创作和完成,只有在受众的自觉参与、干预下,甚至只有在受众自我认定的情况下才能体现它的意义、提升它的境界。在传播学理论中,对受众与媒体的关系理解,也存在着从“靶子论”、“自觉论”到现在的“互动论”,即把受众当作消极被动的、任你媒体随意发出的信息就能击中的靶子;把受众当作积极主动的、任他清醒冷静选择媒体信息的自觉存在体;把受众与媒体之间关系当作双方都是积极主动和互相制约互相支撑的联合体。
在电影和话剧《梅兰芳》中,作品的编导等创作者们,应该是遵循着“互动论”的原则在进行他们的艺术实践过程的。他们请来的大牌明星担任主角是进行这个互动的基础,他们把梅兰芳学戏和与老师竞争是进行这个互动的铺垫,他们把梅孟感情戏设计成“婚外恋”、“第三者插足”是进行互动的主干元素,他们把梅兰芳在日寇面前的大义凛然主观上想设计成为核心和高潮部分,但是,由于缺乏讲故事和深入人物内心江塑造人物的扎实基本功,于是现在只能用一个青年日本军官的自杀(电影)和一个汉奸张牙舞爪的横行(话剧),使得本该让作品大放异彩的部分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作为中国戏曲艺术代表的梅兰芳在人格内涵上最具美学和思想意义的元素被现在的编导解构为话剧影视艺坛上流行的、通俗的“贺岁片”、“贺岁剧”。所以,从这点说,我是同意“黎明和李宇春都可以胜任演电影梅兰芳”的观点的,此话虽然刻薄,但它毕竟道出了一个真谛,在你这样“虚构”演绎出来的梅兰芳面前,历史中、生活中乃至民族精神中究竟谁是梅兰芳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媒体视觉的“梅兰芳”、编导演中的“梅兰芳”、演员表演演技中的“梅兰芳”――因为,似乎只有他们、只有这些大牌编导、大牌明星而不是梅兰芳本人才能引起受众的青睐。
媒体对受众是态度的!除了适当的迎合之外,在受众被引进既定的传播范围内,你就要展开自己的攻势引领。在这点上,我们要老老实实拜人家西方国家的艺术家们为师。以美国为例,小到动物王国的《狮子王》、中到反映平常百姓的《阿甘正传》、大到《拯救大兵瑞恩》和《西贡小姐》,这些作品大都到中国和世界各地巡演,影响也大,它们表面上“玩艺术”、骨子里“讲政治”;形式上“标新立异”、内容上“棉中藏针”;手段上“世界母题”――撒向人间都是爱、目的上“普世价值”――惟我人权制度“放之四海而皆准”!人家与你玩得痛快时,他的价值观已经“润物细无声”;人家与你聊得高潮时,他的艺术观已经“意识能动地反作用于存在”了……对这一点,我们的一些艺术家要么没发现、要么学不会、要么糊里糊涂地跟着乱起哄;自己的真知灼见、自己的价值取向、自己的民族精神究竟在哪里得到体现和弘扬仍然是个未知数!联系到我们的荧幕、荧屏和舞台的节目,数量很多、质量不行,原应就在于缺乏这根心头的准星!
思考之三:艺术运用这个载体表现的是自己的“艺术天赋”还是民族精神的“浩然正气”?
《梅兰芳》这样的作品,允许虚构,但必须是以不牺牲人物的基本历史的真实为前提。只有还原于生活本来的“梅兰芳”才能在艺术和传播学意义上最具震撼力、最具影响力、最具号召力!表现印度民族领袖的电影大片《圣雄甘地》,编导和演员都是大牌,但是,通过影片的表述所传递给全世界观众的信息却只是一个圣雄!这个圣雄不是演员的“圣雄”、不是演艺界沾沾自喜的票房“圣雄”、更不是用来炫耀和标榜某些不上大雅之堂的“圣雄”!时间已经流失了几十年,但是影片所要告诉人们的圣雄思想、圣雄方略、圣雄伟岸的人格和民族精神却依然没有过时、依然鲜活的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心灵处……《梅兰芳》已经公演,我不知到明年这个时候,受众们除了记得陈凯歌、黎明、章子怡之外还会记得什么?“梅兰芳现象”好像已经很普及,我不知道明年这个时候,受众(特别是青少年受众)到剧场看包括京剧在内的戏曲艺术还要这么费劲么?“梅兰芳话题”好像现在也很热闹,我不知道明年这个时候,包括中国戏曲艺术在内的民族文化的很多瑰宝能否运用更多的传播形式的手段达到弘扬民族精神的目的?
这里,就产生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化了那么大的投资和精力去打造一个大片、一部大戏,是制作人、创作者个体的魅力重要还是主人翁的精神世界、特别是通过主人翁精神世界表现的浩然正气重要?按理说,两者是可以不对立的;即是说,通过制作人、创作者编导演的“艺术天赋”这个手段和载体把主人翁民族精神的“浩然正气”淋漓尽致地反映出来、表达出来、展现出来。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两者缺一不可;而且特别在当代,前者的重要性没有人否定。就像电影《黄金甲》因为有了周杰伦的最后加盟虽然得罪了周润发但却赢得了高票房一样。但是,两者的关系绝对不能颠倒!也就是说,传播的形式再高明,没有思想的放送是空洞的;传播的明星再耀眼,没有灵魂的表演是干瘪的!《黄金甲》男女老少明星全了,投资大了,票房高了,张艺谋也一再声称菊花万千的画面“不是电脑合成而是实景拍摄的”,但是除了一个照搬话剧《雷雨》的情节之外,《黄金甲》在思想和审美意义上还能够留给受众的是什么呢?
有人会说,“《梅兰芳》是艺术片,不是传记片,不要给它太沉重的思想主题。”那我就要问了:“《集结号》是贺岁片吗?贺岁片都可以承受这么沉重的思想主题,那么像梅兰芳这样一位扬名世界的艺术家就可以随意的说三道四了吗?”作品中的人物台词反复强调:我们虽然是戏子,但我们也要给这个职业注入尊严的内涵;但是,从戏子到伟大的艺术家之间的一个活生生的心路历程已经基本具备雏形却为什么在你们手中却石沉大海?让人遗憾的是,无论是电影还是话剧,我们看见的只是从戏子走向、走近艺术家的梅兰芳,而不是一位已经完成从戏子到艺术家伟大转变的梅兰芳。
其实,美国演出只是梅兰芳出访生涯的一个部分;梅兰芳曾经带领着梅家班几度走出国门。1935年,梅兰芳奔赴苏联演出,同样大获成功。而具有文化关联性的日本,更对梅兰芳的艺术推崇不已。1955年,梅兰芳率中国京剧团在北欧五国巡演,观众达五万余人次。戏剧专家说“梅兰芳在世界上的影响前无古人,迄今亦尚无来者”。在美国,胡佛总统为演出成功发贺信,卓别林从《城市之光》片场穿着戏服匆匆赶来拜见“偶像”;在原苏联,斯大林、莫洛托夫、高尔基等齐来看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爱森斯坦等艺术大师与其相谈甚欢;在欧洲,他被国际舞蹈协会授予“国际杰出艺术家”勋章;在日本,最好的歌舞伎以被称为“日本的梅兰芳”为荣……这种对各国主流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这种演艺体系被尊重,这种人格完美被提升,我以为,还有更多的是他的演艺理论和以戏曲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被发现、被挖掘、被整理、被继承、被革新的原因,这样的宏大背景在《梅兰芳》创作中被淡化、被虚化、被浮华,那么,剩下的只有一个前半部还可以、后半部不了了之的电影《梅兰芳》,也就不足为奇了。
“梅兰芳现象”的传播,刚刚开了头;希望有志之士能够共同探讨、共同努力――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复兴,为我们民族精神的振兴,为我们民族辉煌的自信!
(编辑/子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