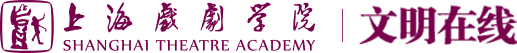最近有学者在讨论上海戏曲30年,我也来凑凑热闹。讲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挑几根“刺”,说一些批评的意见。
多年以前,在白玉兰论坛上,我曾斗胆给上海戏曲号脉,画出了“八有”与“八缺”的脉象:即一是有热情,缺激情;二是有“贼心”,缺“贼胆”;三是有高人,缺高见;四是有“大腕”,缺大家;五是有机会,缺机制;六是有财力,缺眼力;七是有戏迷,缺戏友;八是有大制作,缺大作。
如今,多少年过去了,上海戏曲的面貌改观了多少,我依然不太乐观。举一个例子,探索中前进的上海戏曲一直有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弊端。长的是传统戏整理与改编,新编历史剧、故事剧创作;短的是戏曲现代戏创作。以擅长表现现代生活的沪剧为例,早年有《芦荡火种》、《自有后来人》、《罗汉钱》等一批有全国影响的力作,然而,这三十年间却鲜见深刻反映时代本质与丰富人文内涵的作品。事实上,上海这三十年的发展为全世界所瞩目,这座伟大的城市包括上海郊区几乎每天都会有精彩的故事在发生,但你停神一想,三十年来,有哪一部为上海人所耳熟能详的反映这一伟大变革的沪剧(包括其他剧种)作品能留下来?答案无疑是残酷的。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多,有编剧原创力萎缩、想象力贫乏、观念滞后、远离生活的问题,也有文艺体制机制的问题。
不怕有“塞私货”之嫌,说一点我个人的经历与感受。这三十年,我一直在坚持做一件事,试图追记上海农民三十年的心灵史。从1979年上演《追求》,到81年在《解放日报》连载《定心丸》,到后来的《田园三部曲》,一直到近年的《秋嫂》、《母亲》、《浪漫的村庄》、《大上海郊外的晚上》,还包括十几部短剧,都力图在为上海农民造像,但遗憾的是,在我已上演的28部大戏中,有许多直接反映上海农民生活的剧本也大都是被外省市院团上演的,这样的“错位”必然会带来艺术上有些“水土不服”的副作用,但我无能为力。
第二层意思,栽几朵“花”,说说上海的戏曲教育。上海的戏曲教育主要由上海戏剧学院以及其所属的中专上海戏曲学校承担。三十年来,上戏与戏校对上海戏曲事业主要作出了三个方面的贡献:
一是理论输出。上戏拥有一批一流的戏曲史论专家,特别在对中国古代戏曲史的研究上,成就卓著。还有在上世纪80年代戏剧观的讨论与对“戏曲危机论”的理论反应等重大戏剧理论问题上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二是人才培养。戏校一直有京、昆、越、沪、淮等各专业的表演班,教学成果累累。近年受文化部委托,又在培养昆丑、昆净、戏曲音乐人才等稀缺行当。上戏在编剧人才培养方面,除了常规的四年制本科教学之外,30年间举办了近10期高编班,为上海乃至全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戏曲编剧人才。
三是机制探索。上戏“戏剧大道”的理念与实践,青年京昆剧团的成立,戏曲导演本科班师生独立创作与制作京剧《培尔?京特》的尝试,也为上海戏曲体制机制改革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参照。
当然,作为承担着在源头上培养具有原创能力的戏曲工作者这一历史重任的教学单位,上戏人还需进一步明确自己的责任担当,还需一代一代人去付出不懈的努力。
我期盼着,在新的年代开始的时候,上海的戏曲改革能拥有更宽广的胸怀,能创造更和谐的环境,能出现更生动的气象。
(编辑/子鱼)